发布时间:2019-04-03
一百多年前,作家司汤达写了本书,取名《于连》后改名为《红与黑》,副标题“1830年纪事”。他说:“红,是军队的红色服装,是通往军队获得升迁的途径。黑,是教会的黑色道袍,是通过念神学院、做教士从而晋升上流社会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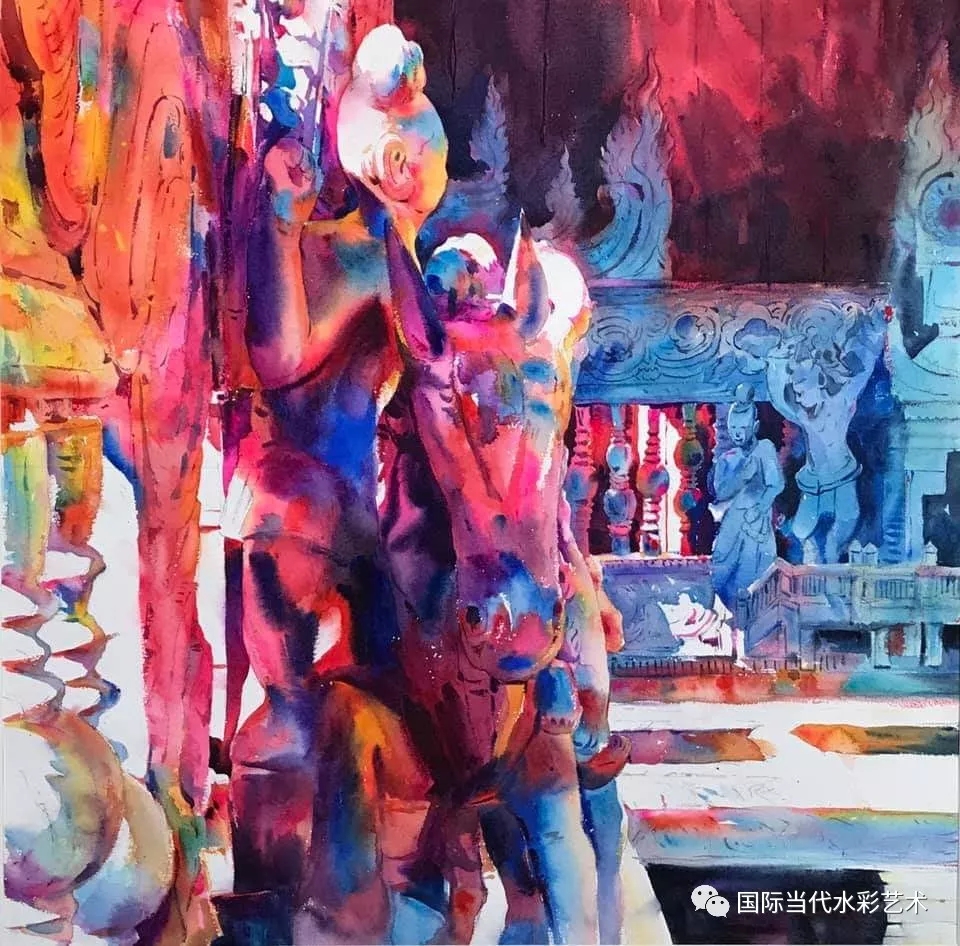
红与黑,是摆在主人公于连面前的两条路。
《红与黑》里,他是红,出身微贱,才华无从发挥,理想不能实现。于是,红带着勃勃野心,孤身一人在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置身黑里摸爬扑腾,手段卑鄙下作。世界上有像庄子那样,“宁生而曳尾涂中”,无欲无求的人,也就会有像美剧《纸牌屋》里安德伍德夫妇那样追名逐利,善于玩弄权术,并乐在其中的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活法,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在于你如何选择。
春光已经乍泄的时节今天是国际水彩500期的日子,还是像以往一样,说几句开场白。春天会给人无尽遐想,劳动的开始也是在春天,每一滴汗水都会给秋天的土地留下不一样的收获。500期是实实在在一期期编辑出来的,是无数的日夜通过团队的努力给予喜爱水彩的人的全部奉献。如果有一句话来表达内心:“那就是致那些没有水彩书籍的日子和那些执着于水彩画的人们”。当内心的火热被一件自己挚爱的事业所吸引,如同陷入无尽的热恋,那种期待和冲动,执着与贪婪诱惑着我们越走越远。网络时代打开了知识的宝库,让我们了解更多优秀的珍贵的资源,边界和便捷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贪婪和野心以及黑暗浑浊的涌流。中国艺术圈自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在自我意淫的状态下飘忽然的以极其低端的方式在追寻着自我的高潮,无论是当代还是传统,一群生产者或在宇宙之端高喊着连宙斯和玉皇大帝都感到恐慌的经语,另一群人如汽车人和霸天虎们遁于世间期待着自己身体的变形思想的升华再去接受宇宙之端的召唤。
艺术之于这社会的每一个人有时很近有时又是非常远。坐在金色大厅听一场民族唱法的音乐会所有鼓掌的外国人几乎不会说出“再来一曲“,所有来听中国京剧的外国人更多是带着对东方人角色身段的垂涎而表现的”温文尔雅“他们绝对听不懂更不明白这些故事。民族的不是国际的,民族的只能是民族的。管风琴到现在在中国几乎没有,修理更不消说。钟表艺术在中国几乎没有,铸铜好像是明朝的那些事,高温瓷欧洲不会烧,抱着自己的梅森瓷却也仍然陶醉不已,我们是在圆的基础上画,画的不亦乐乎再去烧,欧洲人是一定要以光影和解剖为指导来塑造,栩栩如生不是文言文里说的,因此这些文化无法共通,所以在彼此欣赏的时候多数也是”装“。“装”在当下已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了,从国际到本土、庙堂到街巷,无处不在的都在”装“。一部好车里没有行车记录仪你敢开上路吗?因为路上“装”的人会时不时的暗算你一下。一个官位显赫的领导”装“的能够全身而退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高速发展的社会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装“。于连要成功的本性是“装”。一个不会装的艺术家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艺术家。“装”靠什么,前提就是像《红与黑》的于连那样的几部曲,这俨然也是今天艺术“成功”的必备品。
回来再谈水彩这门艺术,20年前艺术家带着无尽的爱投入到其中用“真”唤醒了一代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很多的汽车人在“真”中隐忍了20年,遇见了“装”,面对权利头衔物质他们迎头进入了“装”的队伍。用各种华丽的台词来包裹自己裸露的干躯,有了“装”也有了直面那宇宙狂风和面对巨浪拍袭的勇气,他们无所畏惧,用马“装”鹿,以黑当白,更有后来者哭喊着咆哮着亦脱下“真”的外衣愉悦的等着“装”后高潮的到来,也就有了每天社交软件上那些无数的赞,无与伦比的赞、泪雨倾盆的赞、狂飙掣响的赞,宇宙难容的赞,尿哭破胆的赞。当下的水彩是青红皂白混在一起的时代,“大道至简”非常恰当的进入到了无数500人的群里被无数的“装”和“赞”碾压的时代。
“真”的当下,并不是追名逐利本身,而是原本纯良的,却逼自己进入一个勾心斗角的世界。
彩不再,“水”横流。




